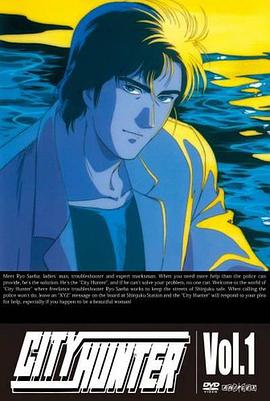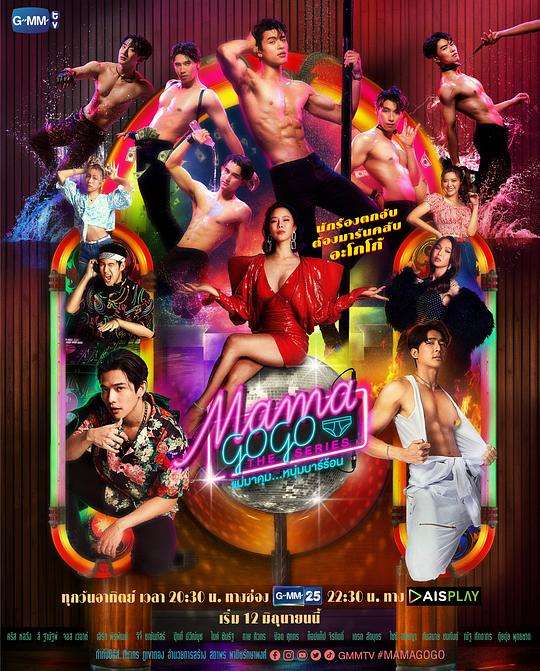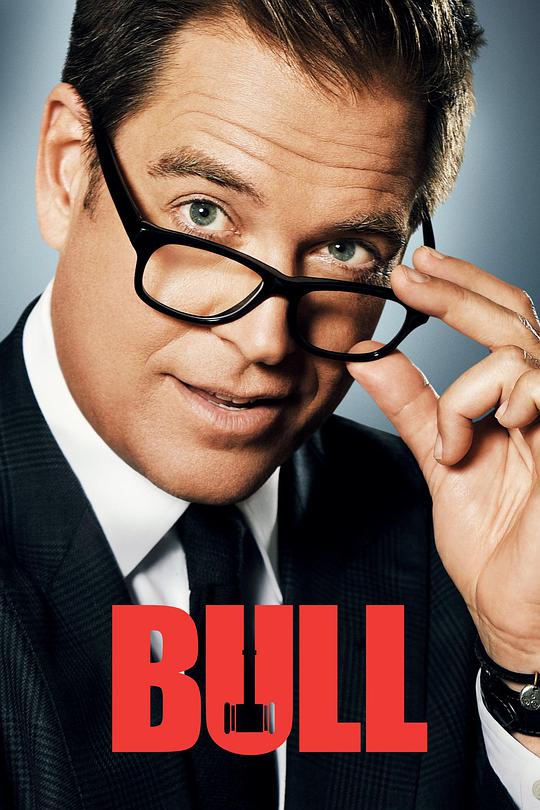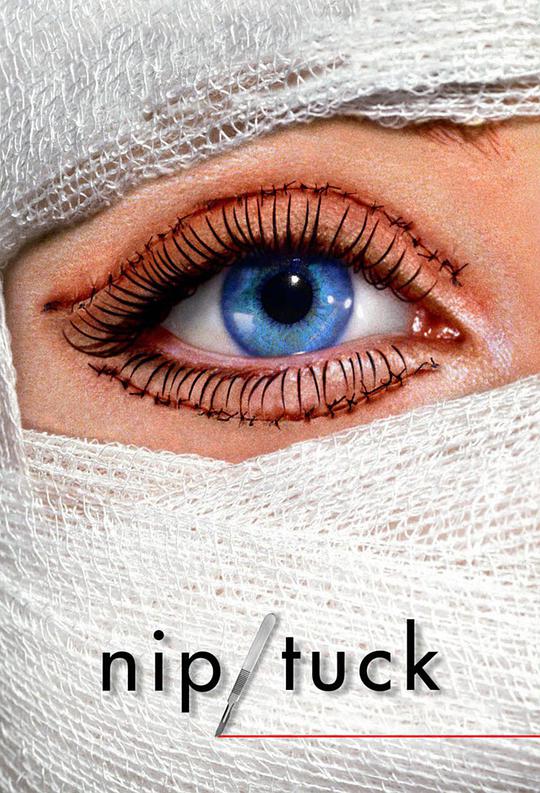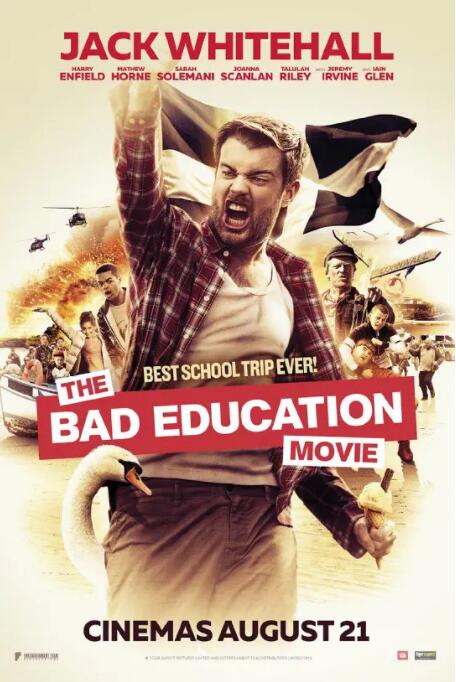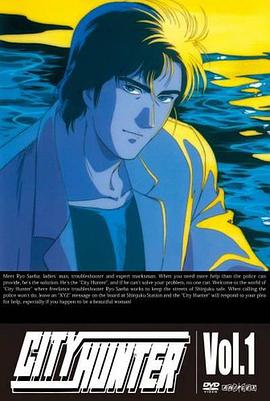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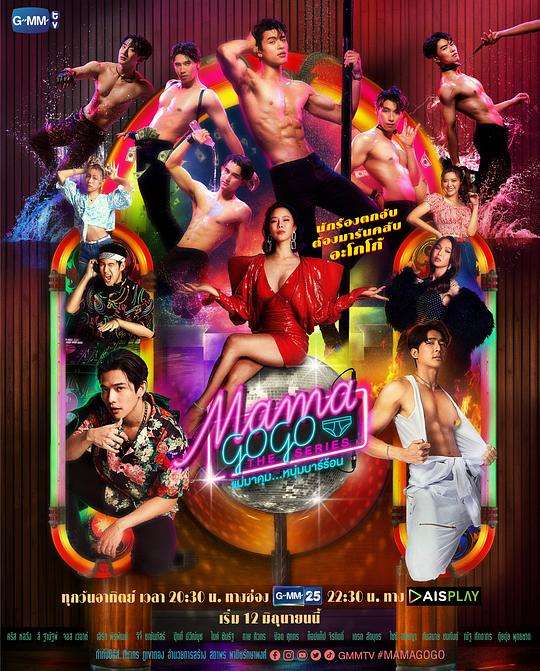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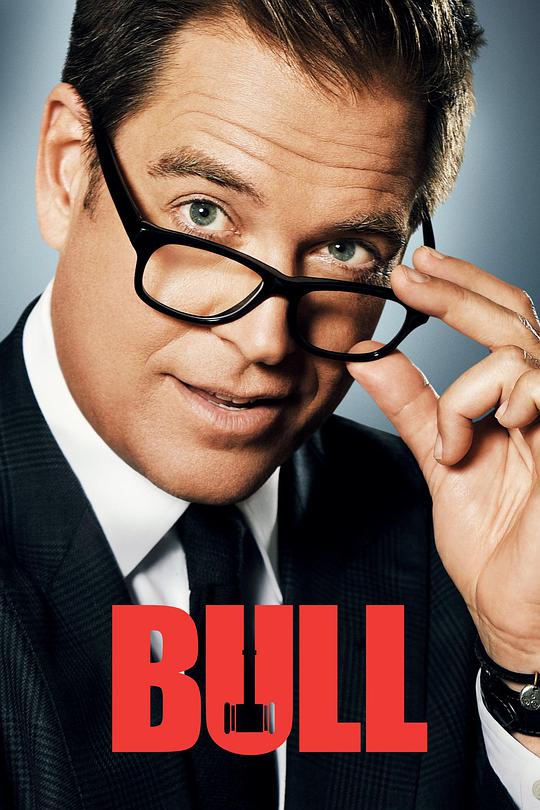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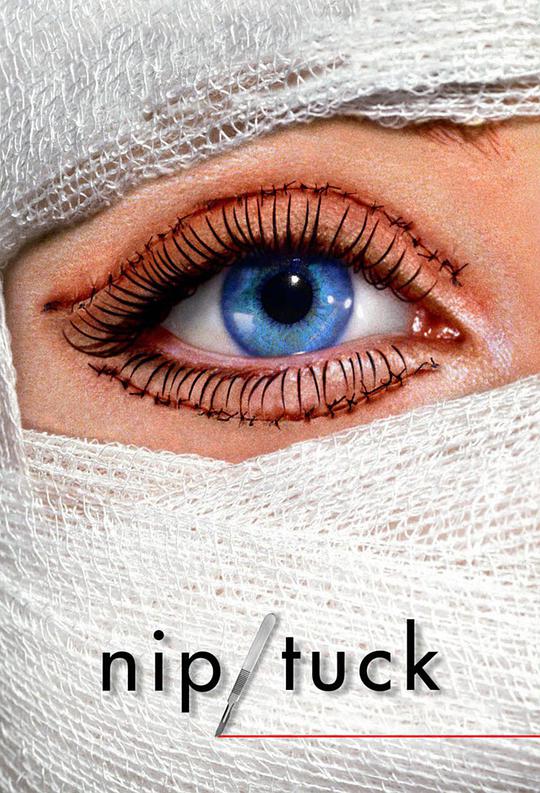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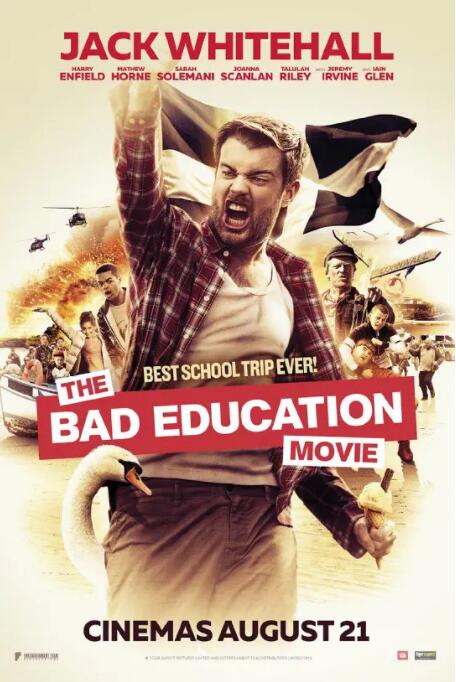



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调节性T细胞的开创性工作,使得很多生物医学界人士觉得看不懂:怎么大领域还没颁过奖,就发小领域?免疫调节的分子和细胞通路众多,为什么专挑调节性T细胞?本文作者深追调节性T细胞的研究历史后,通过该领域走了整整十年的弯路揭示出今年生医诺奖工作乏人注意的独特深刻之处,并借此分析,妨碍中国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原因还有什么因素是没有被充分关注到的?
撰文 | 周大鹏(同济大学教育部病原体与宿主相互作用重点实验室)
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发给了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表彰他们在调节性T细胞的开创性发现。
调节性T细胞能够防止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机体自身,从而避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免疫学上称为免疫耐受),但是在肿瘤患者身上,调节性T细胞却会促进肿瘤生长,因为它会抑制“免疫监视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免疫监视细胞是免疫系统中的“哨兵”和“巡逻兵”,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如癌细胞或病毒感染的细胞),维持机体的健康。
因为已经有很多讲解调节性T细胞功能和意义的出色的科普文章,本文则从科学探索的源头介绍科学家们在发现调节性T细胞的过程中曾经走过的弯路,并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呈现研究方法的选择有多么重要——不同研究方法会在相关科学的发现中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上百家实验室缘何关门
早期免疫耐受的研究,始于麦克法兰·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提出的克隆选择学说,即免疫细胞在发育阶段会把自身反应性的克隆删除,导致中枢免疫耐受。按照这一理论,人在出生前,免疫系统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能够产生数以百万到千万计、具有随机受体的免疫细胞克隆,它们来源于同一个原始祖先细胞,具有完全相同的受体。在发育阶段,这一随机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能够识别并攻击自身正常组织成分(自身抗原)的克隆。中枢免疫耐受是免疫系统在发育早期进行的一场“内部集训”,主要任务是删除那些能攻击自身组织、可能引发自身免疫病的克隆,从而确保免疫系统能够区分“自我”与“非我”。
这一理论在196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但是科学探索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因为中枢免疫耐受理论并不能解释人在出生后免疫细胞会在人患病的情况下对自身组织的杀伤,说明有部分自身反应性的免疫细胞逃逸了中枢免疫耐受。那么怎么解决这些“漏网之鱼”带来的“敌我不分”呢?
1960年代,巴茹·贝纳塞拉夫(Baruj Benacerraf)提出免疫应答的遗传基因控制理论,在此基础上,理查德·格森(RichardGershon)等科学家在1970年代提出抑制性T细胞并“发现”了在机体出生后发挥免疫抑制的遗传位点,这一位点上的基因为 I-J“基因”。表达 I-J基因的T细胞则命名为抑制性T细胞(Suppressive T cells)。
围绕 I-J 遗传位点,上百家课题组产出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谁能发现发挥免疫抑制的I-J基因,就可以指导人类防治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夺去香港女演员周海媚生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可能研发出克服癌症患者免疫耐受的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然而,当时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观察不同品系的小鼠在抗原免疫时产生抗体应答的强弱。今天回顾下来,显然产生抗体应答的影响因素太多,不但包括遗传学位点,而且包括机体的健康状态、机体肠道菌群、机体神经系统的调节等等。一个常识就是人们接种疫苗时,医护人员会询问健康情况,有感冒、发烧、腹泻等症状者,一定要暂缓接种,因为这些非遗传的因素会导致抗体应答的失败。
I-J基因研究的致命伤在于其研究方法选取了高度复杂的表型(抗体应答的强弱)作为衡量指标。在研究方法经不起推敲的情况下,大量研究人员像大合唱一样支持 I-J,这一遗传位点得到了主流免疫学届的广泛认可,大量有志青年纷纷加入,竞相追逐免疫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种通过复杂表型反推单一遗传位点的方法,在当时基因测序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导致了科学界巨大的群体性偏差。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基因测序技术发明后,测序仪器和技术的引领者、著名的莱诺·伊·胡德(Leroy E.Hood)组织研究生对 I-J这个遗传位点进行了全部基因测序和分析。大失所望的是,在分析了每一个DNA片段后,他们发现I- J遗传学位点根本没有什么功能基因。这一令人惊讶的结果导致了上百家从事I-J研究的实验室关门,因为他们之前积累的所有“研究基础”全部不存在了,除了极个别在NIH工作的不需要申请经费的科学家,多数I-J研究者毅然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四十年后,莱诺·伊·胡德和复旦大学合作,创办了《表型组学》(Phenomics)杂志,其动机可能也源自对于疾病表型复杂性的深刻切身体会。
坂口志文的突围
在I-J基因被证明不存在后,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顶着极大的压力,对“抑制性T细胞”的理论进行了修正。
坂口志文发现,小鼠淋巴结和脾脏中有一小群特殊的 T 细胞。它们的细胞表面同时带有CD4和CD25两种特定的分子“标签”。当时这些标签本身的意义还不清楚,但正是这一外在特征,让他得以将这类细胞区分出来,并进一步发现它们具有抑制免疫反应的重要作用。坂口志文发现,如果把这群同时表达CD4和CD25的T细胞从表达CD4的 T细胞中删除之后,注射到没有胸腺(T细胞发育必需的场所)的小鼠身体里,只表达CD4的T细胞会诱导严重的自身免疫病;如果把这群表达CD4和CD25的T细胞注射到没有胸腺和T细胞的小鼠,则不会导致自身免疫病;最为惊讶的是,把同时表达CD4和CD25的T细胞和删除这群细胞的外周T细胞混合之后注射到没有胸腺和T细胞的小鼠,会抑制只表达CD4的T细胞诱发的自身免疫病,并且有剂量效应。这个非常干净的实验明确证明了同时表达CD4和CD25表面标志的T细胞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吸取之前“抑制性T细胞”的教训,坂口志文把这群T细胞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
图1 外周淋巴结含有调节性T细胞和效应T细胞。上图为删除CD4+CD25+ 的调节性T细胞之后的T细胞移植实验,下图为把CD4+CD25+的调节性T细胞和删除这群细胞的T细胞混合之后再进行T细胞移植试验。科学家对比后发现了调节性T细胞抑制自身免疫杀伤的功能。| 作者制图
提出调节性T细胞的理论并发现这一细胞亚群,使得坂口志文毫无争议地成为调节性T细胞之父。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并非无差别的免疫抑制,而是区分敌我的特异性免疫耐受。调节性T细胞在胸腺发育过程中识别了自身组织抗原,在外周再遇到自身抗原时被激活,并抑制其他免疫细胞,彻底挑战了当时“识别自身抗原的T细胞在胸腺(中枢)被删除”的传统观点。
而2025年得奖的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Mary E. Brunkow)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之所以能够成功发现调节性T细胞产生的遗传学机制,显然是采用了更严谨、更可靠的小鼠品系 Scurfy。
这两位企业科学家的目标是治愈自身免疫性疾病,采用的研究工具是Scurfy小鼠。这是一个雄性小鼠发病的品系,其致病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由于雄性小鼠仅有一条X染色体,该基因缺陷会完全表达,导致其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器官,引发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这些小鼠只能存活数周。
Scurfy小鼠的疾病有非常明确的遗传方式:该疾病只影响雄鼠,并且是由母鼠传递的。这是典型的X连锁隐性遗传 模式。这意味着致病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雌鼠有两条X染色体,如果只有一个拷贝突变,它们是健康的携带者。而雄鼠只有一条X染色体,如果这条X染色体携带突变,就必然会发病。这个初步观察将搜寻范围从整个基因组大幅缩小到了X染色体。
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广泛使用之前,怎样在小鼠X染色体上找到Scurfy小鼠的准确位点呢?
这里要介绍一下遗传连锁分析技术,就是遗传学家们已经给小鼠的染色体像尺子一样标注了遗传标记,为了寻找疾病位点在哪个遗传标记附近,可以让患病小鼠和一个健康小鼠(但是来自不同的小鼠品系)繁殖产生很多后代。因为品系的不同,这两种小鼠的染色体尺子上的遗传标记是有差异的,打比方说基因是一个个具有不同功能的人,附近的遗传标记就像一个个人的汽车牌照。在染色体尺子的同样位置,不同品系小鼠的基因如果有不同,比如小鼠毛发的颜色不同,和毛发颜色基因相关的遗传标记(汽车牌照)也是不同的。同一染色体在不同品系小鼠杂交的时候会有来自父系和母系的染色体交换的现象,但是当两个遗传标记靠在一起很近的时候,就很难发生交换,遗传学上称为连锁。我们把致病基因比作变成罪犯的人,把染色体尺子上的遗传标记比作汽车牌照,那么距离罪犯最近的遗传标记就像和疾病(有罪犯)一起出现的汽车牌照。在科学家分析了很多后代成员后,发现罪犯们总是和一个特定的汽车牌照一起出现,就可以确定距离罪犯最近的遗传标记(位点)。
图2: 2025 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通过遗传学的连锁分析,确定了 Scurfy(F oxP3)基因两侧的遗传标记(基因多态性位点,类似和罪犯一起出现的“汽车牌照”),锁定了“罪犯”基因位于一段500 kb的区域,然后逐个排查这一区域的20个基因 (下图)。参考文献:Nat Genet. 2001 Jan;27(1):68-73. doi: 10.1038/83784. | 作者制图
在遗传位点附近进行逐个基因排查后,两位科学家终于在2001年找到了突变的致病基因——FoxP3。在人类身上,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遗传学疾病 IPEX综合症,即免疫失调-多内分泌腺病-肠病- X连锁综合症。对FoxP3的这一发现将自身免疫疾病的复杂表型首次从基因层面与特定的调控分子紧密连接起来。
然而,他们当时并未完全了解这个基因的具体细胞学角色。最终,是坂口志文在2003年将这两项独立发现联系起来,他证明FoxP3基因正是调控他于1995年所发现的调节性T细胞发育与功能的主控基因。这标志着该领域从细胞发现进入了功能与机制的系统解析阶段。
二十年后,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得患者的全基因组测序费用降低到两万人民币,可以很容易发现 FoxP3 突变这样的遗传学疾病。但是这颗免疫学“皇冠上的明珠”,在测序仪器和技术发展初期,依靠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得以早早地发现,并极大推动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的防治。
调节性T细胞为什么值得一个诺奖?
讲到这里,也许质疑者仍然会问,调节性T细胞的这段跌宕的发现之旅真的就是医学意义上排名靠前、值得获诺奖的最重要的因素吗?针对调节性T细胞的抗体药物和细胞药物目前还处于研发初期,并未达到疗效显著获得批准上市的阶段。
在笔者本科教学使用的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版《医学免疫学》教材上,除了调节性T细胞,还介绍了外周免疫耐受的其他机制,包括免疫细胞的克隆失能——免疫学家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和罗纳德·施瓦兹( Ronald Schwartz)发现的免疫细胞在刺激信号不完整的情况下发生的功能失活状态,学界有人认为也是值得授予诺贝尔奖的工作。
笔者认为,诺贝尔奖评委会今年把奖授予外周免疫耐受的调节性T细胞,和大量临床医学单细胞测序发现有关,尤其是在患者肿瘤组织和自身免疫病变组织的单细胞测序数据大量涌现之后,支持了调节性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的功能。如果不是井喷的几千篇测序文章支持,也许诺贝尔奖评委会还会再观望十年,如果出现百亿美元品种的针对调节性T细胞的药物,说不定获奖人选会有变数。
在从0到1的发现之旅上,一个不受关注但致命的因素
每年的诺奖季都会引发诸多反思,很多人追问,为何我国的科研土壤还没产出“坂口志文”?
有人从文化品质层面去找原因,认为我国学术界缺少独立自主的长期主义精神,自甘做从1到100(下称“1-100”)的工作,以换取短期的“自然指数”、“影响因子”,然后结题交差。但是笔者想指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部门分割。
比如,二十年前我国同时期开始的测序工程,在有测序能力,也买得起小鼠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测Scurfy小鼠?因为我国最顶尖的测序人员缺少玛丽·布伦科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的跨部门有效沟通的能力,测序的做测序,遗传的做遗传,不可能形成深度合作关系。但是这一条路线是笔者更关注的路线。
西方科学家也特别擅长借助工业化的威力进行大规模地毯式排查的研究范式。在通过测序找到FoxP3基因之后,即使没有坂口志文,总会有人发现表达这个基因的T细胞,因而发现调节性T细胞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没有测序的验证,坂口志文就始终找不到打开调节性T细胞发育的关键开关,无法从分子和信号转导机制解释这类细胞的真正功能,所以笔者倾向于认同测序工作在今年的诺奖工作中的作用是更加重要的。这个测序工作已经被评奖列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测序工作之列,也是跨部门合作的典范。玛丽·布伦科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分子遗传学训练,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了免疫学训练。欧美科学家跨部门合作的习惯和基因,促进了对 Scurfy疾病位点的测序工作。笔者认为,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在博士毕业后,发表了一系列探索外周免疫耐受机制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这个从0到1(下称“0-1”)的问题在探索,这一点起了主要领导作用。
在玛丽·布伦科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发现了 FoxP3基因后,日本政府按照文部科学省《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战略部署,通过资助各种突出调节性T细胞的学术活动,帮助坂口志文扩大影响力,鼓励CNS正刊和子刊井喷了数千篇在临床患者组织中发现调节性细胞的测序文章 。而且日本自己不投入,在激烈的全球经济和科技战争中消耗他国资源。例如在2020年8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向全球发布了一份关于科学技术创新的报告“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2”,称赞无论是在论文数量还是高质量论文上,中国现在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均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通过鼓励中国为日本投入1-100,让他人举国测序支持坂口志文,再达到以战养战的功效。
从笔者的视角来看,我国生物医学领域当前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对工业化思维与系统工程方法论的理解与应用不足。在科研实践中,常见的是学术领袖以个人力量推动某一研究方向的规模化,但这种推动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整合,与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所体现的深度协作存在差距。相比之下,国内在短平快、“产出高”的方向上,如纳米、结构生物学、信号转导、测序、化学合成等领域往往各自为阵,形成“规模第一”的研究群体,但缺乏整体战略和系统协调,组织的主要是虚头巴脑的假“交叉学科”:领导者脱离科研一线,青年骨干疲于奔命忙于绩效考核,没有条件达到攻克0-1问题的深度整合。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科研体系在方法论上的薄弱。
如果只选拔解决从1-100问题而不是攻关0-1问题的选手,通过这种竞技模式产出的,显然是最善于为局部利益夺取资源、并且占用其他部门资源的选手,对于产出0-1问题所需要的复杂系统,则起破坏作用。1-100工作的自然指数越高,对外国人创造0-1突破性发现的支持越高。而今年上述三位诺奖得主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根本提都不提那几千篇支持自己拿奖的1-100的论文,客观上也没法致谢。这些1-100的文章也没有给产业带来什么贡献,一窝蜂在卷的是仿制欧美已经获批的药物,没有可以抄的调节性T细胞的药物。
如果我们对比由国家强力整合最顶尖力量联合攻关、在纪律上不允许谁算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青蒿素(523工程)、糖丸疫苗这些示范项目的投入,和过去二十年山头林立、以考核帽子、项目、规模为导向的万亿投入后拿不出0-1产出的事实和数据,真相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的文化土壤是“枪打出头鸟”,那么出于自我保护,大家都要避免成为“主意与本事不相符”的异类。而钱学森所强调的系统论,则是现代科学中基础而关键的方法论,对推动长期、可持续的科研创新至关重要。相信当纠正了方法之后,我国肯定还是能够再次做出有诺奖水准的0-1的突破性重大发现的。
注:本文封面图片来自版权图库,转载使用可能引发版权纠纷。
特 别 提 示
1. 进入『返朴』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精品专栏“,可查阅不同主题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朴』提供按月检索文章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类推。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摘编。转载授权请在「返朴」微信公众号内联系后台。